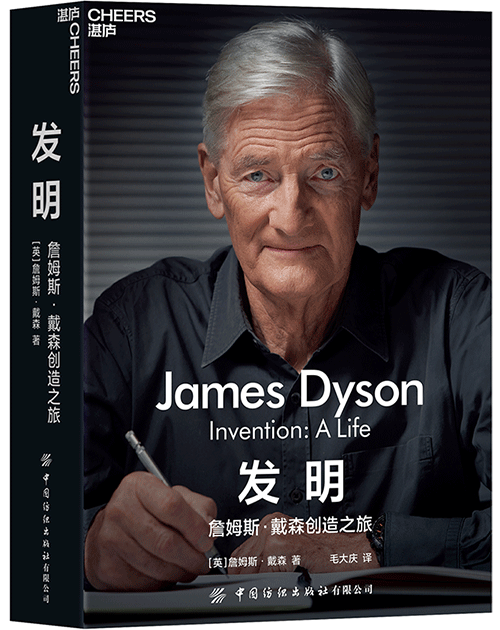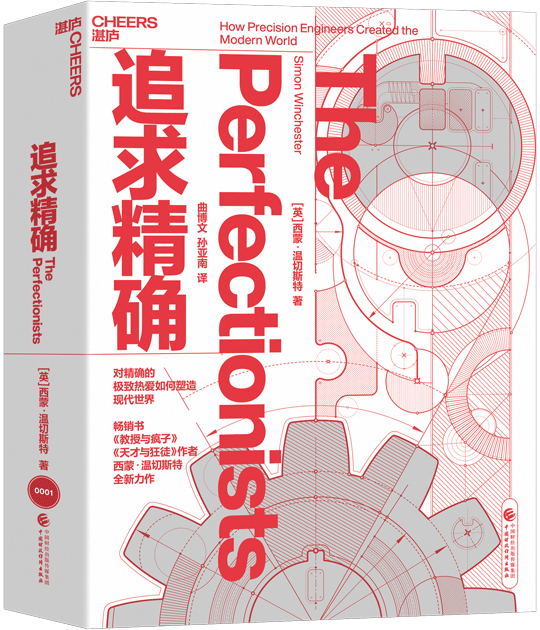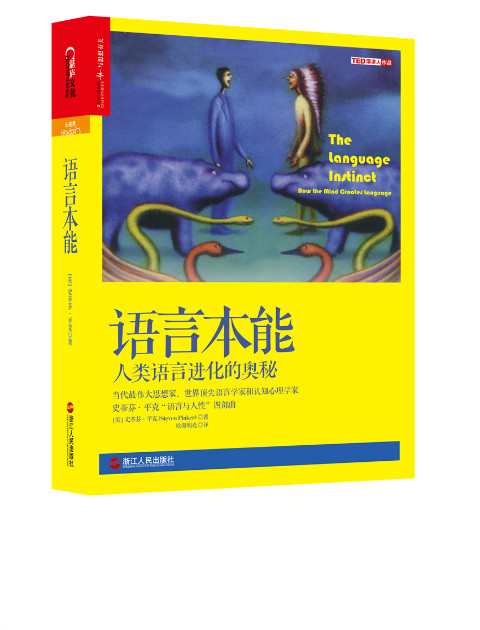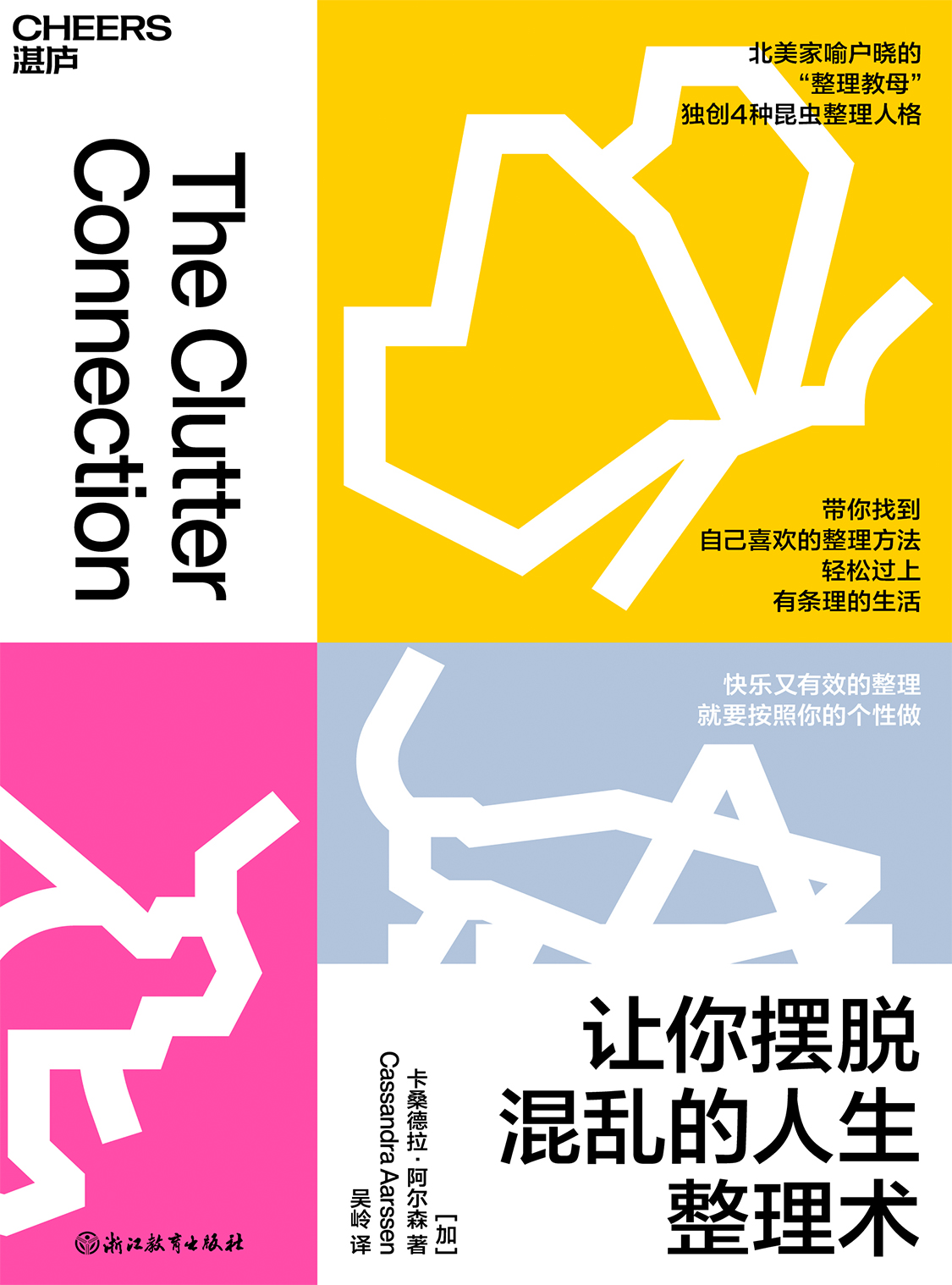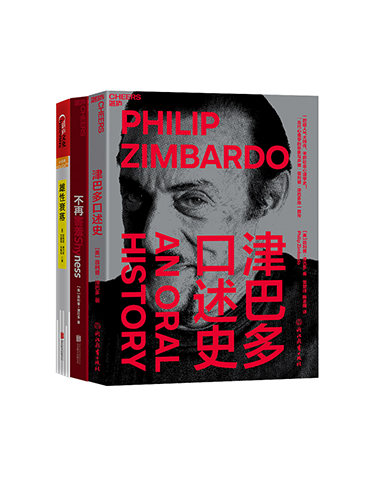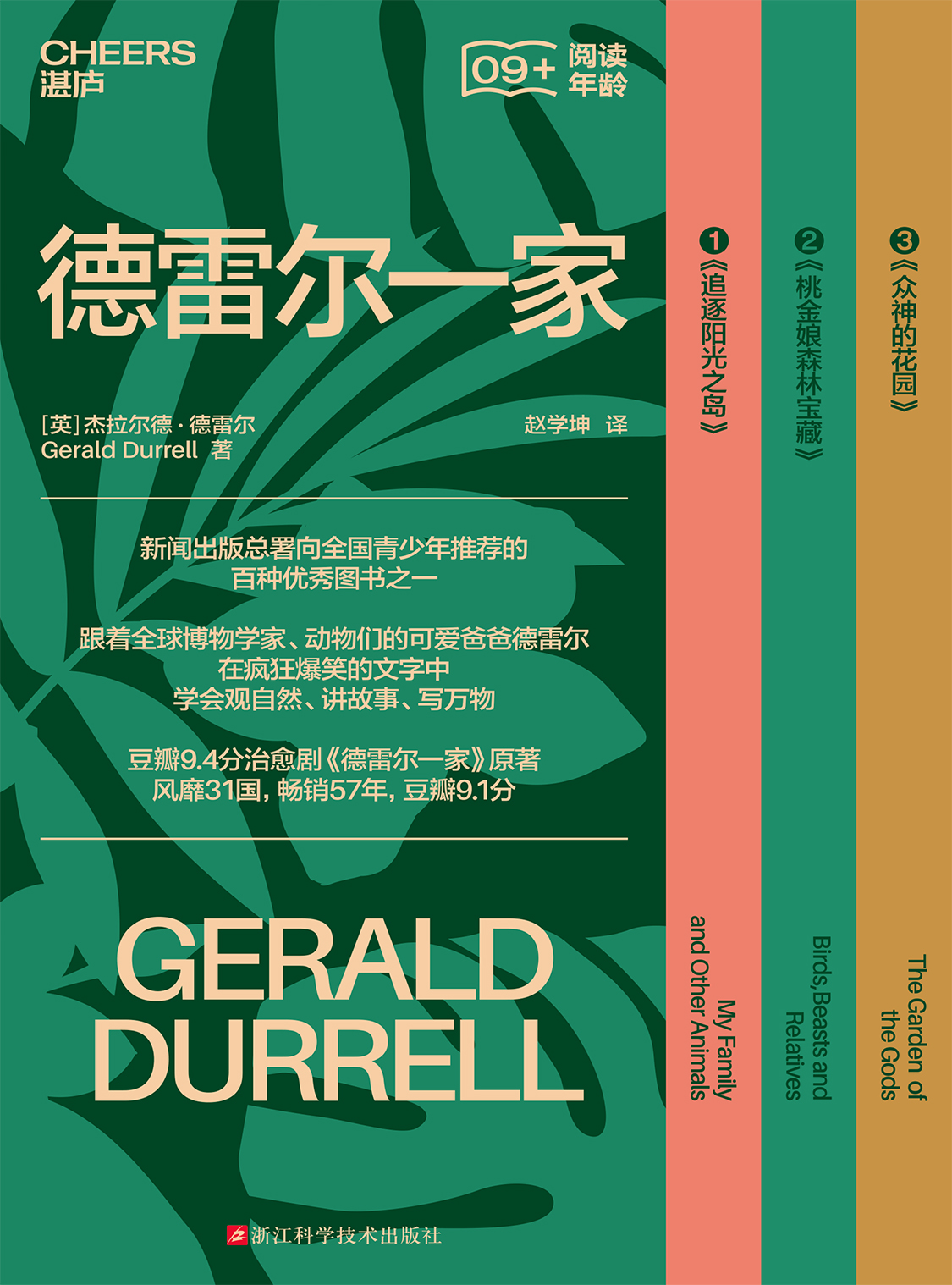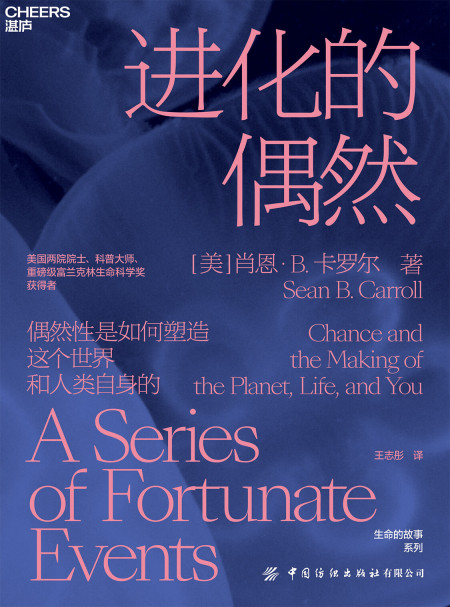
偶然性是如何塑造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的?
向你展示“偶然“在进化中的强大造物之力
美国两院院士、科普大师、富兰克林生命科学奖获得者
肖恩·B.卡罗尔重磅新作
【作者简介】
肖恩·B.卡罗尔
美国进化发展生物学家、作家、教育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威斯康星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教授,曾获得富兰克林生命科学奖。
卡罗尔与爱德华·威尔逊、奥利弗·萨克斯和理查德·道金斯等人齐名,是一位备受推崇的科普大师,也是刘易斯·托马斯科学写作奖的得主。
此外,他还担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学电影制片人,所拍摄的科学短片和教育素材被成千上万的学生免费使用。
【内容简介】
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我们为什么存在?
凡事皆有因还是一切皆偶然?
哲学家和神学家为此争论了上千年。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科学发现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偶然”塑造的世界中。
偶然性是如何塑造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在《进化的偶然》一书中,进化生物学家肖恩·卡罗尔从古生物学、地质学、进化生物学、基因科学等众多领域的全新发现入手,结合宏大至小行星撞击地球,微小至基因突变的众多妙趣横生的实证,向你展示“偶然”的强大造物之力。
与此同时,卡罗尔剥茧抽丝地论证困扰达尔文的问题“突变和自然选择,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发明者”,并帮助你厘清突变、自然选择、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各方赞誉】
我一直认为,如果物理学是对的,生命的诞生就是必然的。但我又得承认,每个生命都是一次奇迹,特别是高智能生命的涌现,包括正在看这本书的你。无论你贵贱贫富,妍蚩愚智,都请牢记,你就是历经了千难万险、独一无二的天选之子,无需妄自菲薄。这本有趣的作品,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让我们理解造物之神奇、众生之平等。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整个宇宙的神奇之处,竟然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认知了偶然性的我们,当不断以知识和学习为桥,从偶然中持续发现和把握必然。
尹烨
华大集团CEO
被誉为“发育演化生物学界达尔文”的卡罗尔教授,不仅是成就斐然的生物学和遗传学大家,还是家喻户晓的科普大师,与威尔逊、道金斯齐名。他的《进化的偶然》、《非凡的生物》、《无尽之形最美》三部曲,以恢弘的视角、细腻的笔触、专业的风范,展现了大自然生命孕育、演化的造物神功,勾勒出21世纪演化生物学前沿的华美乐章。
段永朝
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这本书令人着迷且令人兴奋,这是卡罗尔的力作。
比尔·布莱森
科普作家
畅销书《万物简史》作者
在这本书中,卡罗尔完成了一项非凡的壮举。他用智慧和科学严谨地处理了一个大问题,也就是偶然在我们的身体和地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卡罗尔带我们领略了地球历史、DNA、癌症和进化,这是令人敬畏且十分重要的。我有时读着读着就会笑出声。
尼尔·舒宾
古生物学家
进化生物学家
【目录】
引言 偶然带来的麻烦
第一部分 无生命世界的偶然事件
第1章 一切意外的母亲
两个世界的界限
小行星撞击地球
真实的世界毁灭
按下生命的重启键
幸运的撞击
第2章 暴脾气的野兽
好时代,坏时代
世更替的原因
从温室到冰窟
欢迎进入冰川期
地球气候的纤颤
四季皆宜的动物
第二部分 生命内部世界的偶然事件
第3章 自然选择的青睐
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鸽子
自然选择的力量
变异的偶然
第4章 偶然,随机发生的意外
十亿分之一
DNA结构的奥秘
DNA聚合酶,最快最准确的打字员
突变,DNA的特征
第5章 被偶然统治的美丽错误
鸽子如何获得不同的羽冠
DNA的一小步,猛犸象的一大步
突变的创造性
攀登进化的阶梯
偶然的生命之树
第三部分 个人化的偶然事件
第6章 一切母亲的意外
七十万亿分之一
为出生感到幸运
独一无二的运气
自卫的阶梯
免疫力的兵工厂
第7章 一系列不幸事件
癌症发病的阶梯
驱动器型基因突变
癌症的发生是偶然的
与偶然进行斗争
后记 关于偶然的对话
致谢
参考文献
推荐书目
【基本信息】
分类:复杂科学/科普读物
书名:《进化的偶然》
作者:[美]肖恩·B.卡罗尔(Sean B. Carroll)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出版社:湛庐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9787518095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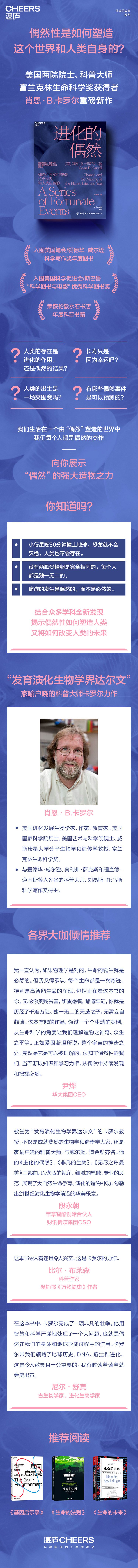
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包括人类自身,原来全都是“偶然”的杰作。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是偶然形成的。